重回二十年前的春节:烟花下的美好回忆

开始写下这第一句时,我正漂浮在飞往三亚的万米高空之上。云下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层叠山峦。伴随着孩子哭声的持续颠簸之后,我身体的战栗和内心的瑟瑟彼此呼应。我坐着西雅图制造的波音飞机,用纽约设计的苹果电脑,听着汉语外语各地方言,敲打着这些方块字组成的句式,内心里想要倾诉的对象却是巨大的铁翼之下那如蚂蚁般大小的村庄和正宗国产的缕缕乡愁。我多希望这条航线经过我的故乡,也许正在麦地里浇春水的父亲一抬头,正好就看到了我。我用意念在飞机左旋或拉烟,让父亲知道我在他头顶之上,也在他浇灌的每一颗麦苗的呼吸中。

时光在云层之上,穿越回到二十年的此刻。
仿佛只有回到故乡,过年这一恍如宗教仪式般的过程,才算完整。
除此之外,在哪儿都是流亡。
冀南大地萧索的平原上覆盖着植物的枯枝败叶,秋收冬藏的农谚里一切悄然轮回。年的脚步一脚踏进腊月,天上的星星都激动地眨了眨眼睛。腊月初八是真正的过年序曲,是春节的第一扇小门,只要一推开心就开始发痒了,抑制不住的兴奋像一只怀孕的母猫再东躲西藏也将暴露无遗。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之后,村庄这口大锅也开始冒出热气。在大小城市打工的中年人会在此后陆陆续续回家,扛着巨大的蛇皮袋风尘仆仆地归来。看到熟人必是要停下来敬颗烟的,还得是村里少见高级的牌子,更熟识的可能还要说几件新鲜事,骂几句赖工资的老板和包工头。
时光向着年的方向一路小跑,腊月二十三便是春节的大门了,这扇大门在甜丝丝的氛围里悄然洞开。记忆中每家都有一个黑洞洞的厨房,老家叫灶屋,小时候做饭都是烧柴火,所谓柴火大多是棉花棵、玉蜀黍芯儿、芝麻杆之类的,只有蒸馒头炖肉才用粗大的树木枝干。现代诗人们笔下最能代表乡愁的炊烟也几乎看不到了,大多改用煤气灶或电磁炉,偶有使用火灶也看不到几缕哀愁了。这一天正是天神派往人间的巡视员,相当于“驻外大使”的灶神回天庭复旨的日子,一年到头烟熏火燎,终于可以回天庭省亲,想必灶王爷也是很高兴的。百姓为了请这位大神上天言好事,为自家美言几句,以求来年兴旺富顺,纷纷买来糖果,叠了纸元宝,剪了金纸银纸奉上,祈得甜心蜜口不负期望。幼时祭灶所用糖瓜是一种酥糖,用糖稀搅白拉成空心细管趁热制作而成的。一咬嘎嘣脆,满嘴流香甜,后来这种吃食逐渐因做工复杂回报低廉而退出了乡野,人们才用水果硬糖代替。祭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那一天必须全家团圆,无人在外,一个都不能少。我自参军往后七年没有在家过小年,母亲竟是足足七年未祭灶,想来真要是有灶王爷,他得多嫉恨我们一家,立即感觉满腹愧疚。第八年我携妻带女回家过小年,买了各种高级巧克力糖果让娘祭灶,愿把亏欠的统统都补上。灶王爷请受小生一拜,前事愿既往不咎,继续美言。

记忆中腊月二十四总是艳阳高照的好日子,也许是我记忆的太阳所投射的光芒映照。这一天要把大件家具都搬到院子里,什么桌椅板凳、电视机缝纫机,母亲会在枣树下一件件擦干净。此刻父亲已经将扫帚绑在了长木棍的顶头,找旧布头遮了嘴脸,扫屋顶和大梁,灰尘雪一样落下来。墙角的蜘蛛网上还留着几只已经干枯的蜘蛛或苍蝇。放寒假的我们兄妹三个也会七手八脚的帮着忙或者添着乱,会从床底下、桌缝里找出丢失了一年的小玩意儿而乐不可支。这一天是要吃小米干饭的,黄橙橙的小米加水上锅蒸,再用猪油炒些白菜浇上,就是一顿妙不可言的美味。

之后一直到大年三十这几天除了蒸包子、馒头、花卷、花糕,还要蒸面鱼、面蛇和一对刺猬,蛇我们叫长虫,长虫和刺猬都驮着小小的元宝。分别有讲究。另外马不停蹄地购置年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巴望着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能带着自己去赶集,去不了县城,乡里的集市也是好的。南去二十多里是县城,那里在幼年是比北京还远的地方,那里有宽宽的街道百货大楼和医院。想一趟都是奢望,我六岁去过一趟,是住院,我从大车上头朝下栽了下来,人事不省。十四岁去过一趟还是住院,因出了车祸,大腿骨折。其他去的时刻便屈指可数,只记得年前满大街的人和刚出锅的酥脆火烧和飘着香菜末的鸡蛋汤。北去五里是小镇,去的比较多,所谓集市平常逢二五七开集,只有一条街外加一个临时买衣服的地摊小市场。小时跟爷爷奶奶都去过,主要是购买过年的零食和菜料。这条街自我有印象起就是沟沟坎坎险象环生东堵西塞,到了年尾更是水泄不通,街旁炸糖糕菜三角萝卜丸子的、翻炒着花生瓜子的、卖葱姜蒜芹菜蒜薹的、卖烟酒糖茶的、现场写对联门心的,最热闹的卖家当是卖鞭炮的,为了聚拢人气宣传自家的鞭炮,过个半小时一刻钟就要燃上一挂,噼里啪啦声中人声更加鼎沸递钱的拿鞭炮的肆意吆喝问答。走饿了,挤到包子铺递上一块钱,五个热气腾腾的包子就用油纸包好了传过来,迫不及待一口咬下去烫得直吸溜吃得最过瘾,好像要把童年所有的欢乐一口吞下去……
有点志玲嗲的广播女声提醒飞机要落地了,收起小桌板调整座椅靠背打开遮光板,我必须从油腻腻的回忆中抽身回来。那时候距离二十多里的县城感觉比北京还远,而我此刻丈量故乡为直线距离两千多公里,然而我依然觉得触手可及。

飞机到达后就马不停蹄去采风,为海南黎族创作一部歌舞剧做准备,先后去了保亭槟榔谷黎族文化公园,五指山和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市三月三非遗公园,寻找黎歌传承艺人,收集黎族故事,也近距离去触摸和嗅闻属于这块土地上的事物的温度和质感。那些苍老的黎族阿婆唱着悠扬的,一个字都听不懂的黎歌,像在召唤某种逝去的时光。考斯特穿行在各种盘山公路上,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橡胶林、香蕉园、高高的椰子树和槟榔树,果实张在枝干上令人匪夷所思的菠萝蜜树,还有怒放的木棉树及云雾环抱的山巅。一闪而过的黄花梨基地和坡鹿保护基地也不能阻止我因晕车而产生的倦怠,这里随处可见的山是故乡没有的山,随处可见的湖或水库也是故乡没有的,树木和水稻也是故乡没有的,念经般神秘又悦耳的黎歌也是故乡所没有的。这里是我吃过的那么多香蕉的故乡,却是我的异乡,我是自我抛弃在属于异乡的土地上。回到三亚住在面朝大海的酒店终于看到了海,这几天来来回钻山林野地似乎忘记了海南是一个岛,走在喧嚣而伤感的海岸线上,我丝毫燃烧不起来任何对于美好生活的热望,也许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梦想漂泊又厌倦漂泊,我渴求未知又为此忧心忡忡,我是一个水火不容的人,我人形的容器里装满了我对世界的偏见和沉默。

旅途中我带了一本书,是美国作家安东尼·多尔的《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故事讲述了二战时期法西斯德国侵占法国时期,德国少年维尔纳和法国少女玛丽洛尔的故事。小说的结构,散文的语言,诗歌的质地,让我总是舍不得读完这本书。仿佛读完了,一切都结束了。可事实上故事已经结束多半个世纪了。我的认知分裂和内心偏执使我不能处理好生活中很多事情,不能全神贯注地去消化眼前的事情,但比从前暖心的记忆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是的,我飞越海南岛到大陆并不宽阔的海峡之时,想继续写完关于年的甜蜜和哀愁。
大年三十这天,欢乐的过山车到达了顶峰。就算是我在回忆这一天都能感觉有点情绪从身体里冒出来,不断涌动在我的心头。一开始总是娘一个人担负起包饺子的大任。孩子渐渐长大后,哥哥开始剁白菜馅儿,先大刀切开,再碎成丁儿,然后双刀并用,直到剁碎。这时电视机里总是播放着诱人的电视剧,剁着剁着就忘记了手下,一阵温柔的斥责后刀光又起。剁好后加五香粉、葱末、盐,拿滚油一泼调匀即大功告成。母亲总是不自信地让别人尝馅儿的咸淡,后来她逐渐丧失了嗅觉,闻不到任何味道,这让我隐隐心疼。我看过荷兰的一部电影叫做《完美感觉》,男女主人公逐渐丧失了味觉、嗅觉、听觉,最后丧失了视觉,而正是丧失使他们懂得珍惜彼此的存在,学会了紧紧相拥。我理解的这种流行病其实就是现代文明的隐喻,文明让人变得不再野蛮,也不再真实和感性。可我不希望我娘丧失任何一种感官,她还没有嗅出这世界最美好的味道呢!接着她开始和面撒剂子,搓成圆柱体,拿刀切大小均匀了,撒成一层面,双手在小面团上平行滚动至半圆,放到手心轻轻一压,便是一个圆圆的面饼。擀面杖上下翻飞,边儿薄底儿厚的面皮儿飞了出来。娘捏饺子是姥姥亲授,自然有姥姥的风范儿,灵秀小巧褶儿多边儿大,一个个士兵般排列在高粱细杆编织而成的圆形托盘上,等于从陆军变成海军。这时爹已经熬好了浆糊,拎着苍老的条凳走到门楣下,撕下上一年残留的对联门神和花纸,虔诚地刷上浆糊一张一张贴好。然后等娘烧上些元宝纸钱才能把请来的神像贴好供奉上,其中最大的神必须在正房(北屋)门口左侧设神坛,按历代制法坐北朝南,年画神像密密麻麻,中书“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位”,正对全神位置的是南海观音,其他是各司其职的神位:厨房里的灶王爷、仓库里的仓官、井边的井神、护佑车的车神门纷纷设坛享受香火祭祀。待到正午十二点,鞭炮声四起,饺子纷纷下锅,鞭炮声是一种欢乐的信号弹,引领着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透出一种对联般的殷红来。我们这些男孩子自告奋勇地担负起放鞭炮的重任,有时会派去给爷爷奶奶家放鞭炮,我就常常燃了长香奔跑着穿过鞭炮声大作的巷子去等待奶奶的指令,她踮着微颤颤的小脚四处拜神祈福,然后对我说,点吧。三十这天放的多是二百响的大地红,我小心翼翼又兴奋又害怕去点挂在枣树上的鞭炮,火舌飞溅丝丝拉拉噼里啪啦,好闻的硝烟味儿飘散在院子里。

写累了,插上耳机听歌,音乐播放的是谢春花的《荒岛》,歌唱着“我听到一只搁浅的蓝鲸,爆裂出巨大的声音”。我怎么会在这里呢?沉默的悬浮着。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之中,精神需求使我们无限地寻求空间,走着走着却发现,我到底在寻找什么呢?此时一回头,来路苍苍,水雾茫茫。
到了黄昏,村庄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再吝啬的人也舍得把所有的灯点亮,因这灯是要照亮未来一年的好光景的。故乡没有年夜饭的概念,各家按喜好吃上一顿,就开始准备守夜和拜年的各种事项。竹筐里堆满花生瓜子糖果,还有孩子们喜欢的糖人和大米花球;藏起剪刀和扫帚;给孩子们找出新衣服放在床头;找一只碗点了蜡烛把面蛇放进水井里飘着,将两只面刺猬放在门沿内侧;大锅烧水洗洗头烫烫脚……忙活完了凑到我们家十七寸星海牌黑白电视机面前,等着冯巩说我想死你们了,等宋祖英唱清亮的山歌,最后等赵本山演绎狡黠的农民积攒一年的笑点。过了十二点,就被父母催促着上床睡觉了,一开始还兴奋得睡不着,想着新衣服和鞭炮,慢慢就撑不住了一个趔趄滑入梦河。

按照我们这一带,具体方圆多少里尚不清楚,都是在正月初一凌晨三点左右,也就是五更天起来拜年,故称“起五更”,可能也是守夜习俗的一种演变,毕竟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就得傻一天。三点左右,炮声大作,火光映天,我们从梦中醒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刻总是朦胧惺忪寒冷又极致温暖的,说寒冷那是正值五九六九时节还是凌晨,刚刚从热乎乎的被窝里钻出来自然的感受。说暖却是多层次的。这一刻根本不用闹钟,因为总有积极分子在两点左右就开始放鞭炮昭示自己起得最早,迎春纳福的诚意最高。炮声就是命令。父母穿衣服起来,还不忘把我们的衣服找出来,害怕我们一会儿要起床大呼小叫找衣服。先要燃起灶火把水烧开,煮了饺子准备上供和吃饭。平常的饺子可荤可素,这五更的饺子必须得是素馅的,多是豆腐胡萝卜加粉条。饺子出锅盛上三碗供给全神,方可挨个拜神烧纸,放这一年最长的一挂鞭炮。孩子再没睡够也顶不住这样的诱惑,纷纷打着哈欠穿新衣服起床。娘总是会嘱咐起五更时不能用剪刀、扫帚,甚至不能大声说话,让这几个小时充满了神秘感。这一时刻必须祥和无比不许吵闹,恐惊了神仙。兄弟姐妹多的打闹起来,父母也得忍住温柔万分地训斥,那是一种奇怪又神秘的氛围。我打小就不爱吃有胡萝卜豆腐的素馅饺子,即便里面包了硬币谁吃到就能大富大贵。我大哥倒是吃过几次,至今还在故乡的大地上辛劳奔命,我却几次躲过死神的扣杀。好赖吃过几个饺子,一家人就整整齐齐出门了,到爷爷奶奶家等大爷大娘一家汇合。即使家中空无一人,也不得关灯关门,不能将任何来拜年的亲眷拒之门外。我总是记得花纸被风吹得哗哗乱响,投射的影子在墙上、地上,在我心里三十年了,还在撩拨我孱弱的回忆。

踩着鞭炮包装的红色纸屑,进入到烟雾缭绕的里屋,父亲带着我们兄弟给祖宗上香磕头,神三鬼四,我们要磕四个响头才能表达儿孙的敬意。桌上已经摆满了供品,瓜果点心花糕饺子,香丛高高低低,烟雾升腾。人群越来越壮大,小时候大爷家三个儿子,父亲的枝头也有我们兄弟俩和妹妹,孙辈也才六个人。时光开枝散叶,良田五亩繁衍重孙累累。大爷家三儿子,娶了三个媳妇,又生下四儿四女,大哥儿女各一,我混迹部队结婚晚产量低,只贡献了一个女儿,四世同堂时二十多口人挤在一间小屋时,理解了什么叫人声鼎沸,感叹生命力的旺盛和时光的步履。大爷或父亲张罗着晚辈们给爷爷奶奶拜年,先是一声“给你们爷爷奶奶拜年了喽,先给你们爷爷拜年”,一呼之下所有人按照自己的辈分称呼着“爹……爷爷……老爷爷……”齐刷刷跪拜在尘埃之地。如同古装剧中皇帝出行到街市上呼啦啦跪倒那一片百姓,必须双膝跪地,方显诚意实意。接着又是给奶奶磕头,老人安然在上接受子孙朝拜。受拜者职责不同,爷爷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谁来都给倒上一盅酒,抽烟的递一支烟。而奶奶此刻要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小时候我们都是一人一块钱,接过新崭崭的钱都舍不得放口袋里怕折出印痕来。按照奶奶的逻辑,发压岁钱不按年龄,没结婚的都是孩子。我是孙辈中结婚最晚的一个,二十七岁那年奶奶还给我发了五块钱,其他领到压岁钱的都是鼻涕都没擦干净的重孙子孙女们,这让我感觉严重拖了老李家繁衍生息的后腿,这几年开始给老人发“孝顺钱”。两军汇合之后便浩荡荡出门,去给李族长辈,多是爷爷的叔伯兄弟拜年去,说着吉祥话,磕着实在头,男则敬香烟斟美酒,女则捧着糖果花生都走出家门了还往孩子口袋里塞,灯火阑珊处欢声笑语在闪着光芒。进门时个儿高的要伸手去够门沿上的刺猬,使刺猬头朝外,临走时把头朝里,意味着送福没有把福带走。一个个家族成群而动,颇有原始社会遗风,在巷子里、大街上遇见了,不顾地上尘土或残雪就一片片跪下来,路灯昏黄,红灯笼在寒风摇曳着,再冷也被驱散了……

降落,摆渡车,地铁,回到我在北京的巢穴。看着房间里的植物枯黄的枝叶心生隐隐,崩溃的电脑带走了许多我写下的文字,幸好记忆还在,找不回来的,我可以再写出来,只要我的呼吸还没有停止或者患上老年痴呆症。我们都生活在巨大差距之中,这种差距被现代文明施以魔咒,我们渴望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却又砍伐森林污染河流几近挖空了亿万年前生长在地球上的动植物凝练的矿藏;我们因惧怕孤独而创建了密不透风环环相扣的大都市,而城市又变成盛放孤独最大的容器;我们利用各种网络社交方式让脚步抵达远方,内心里又总会涌起难以言表的浓郁乡愁。
大年初一的欢歌依旧在大地上高奏,给族亲拜完年之后,年轻后生要汇聚在街头等待更大支系组成的队伍去给德高望重的乡亲拜年,此时再看游行的队伍如同过江之鲫,相互调侃着、打闹着,每个人裤子的膝盖处都是潮湿的泥土,那证明他们为亲情、习俗和这片故土不止一次的下跪过。


初二本是回娘家拜年的日子,早些年我们会跟娘回姥姥家拜年,妹妹出嫁后初二也要回娘家,风俗随着身份转变,初二女儿回家,老闺女就得初三回娘家。这一天一大早,我们兄弟五个(没有妹妹的任务,小时不知道有多羡慕她),要给大姑二姑去拜年,代表娘家人知礼厚亲香火旺盛。兄弟们自由分成两三人一组,顶着寒风呼哧带喘地赶到四五里之外的姑姑家。进屋先褪了手套帽子在火炉上烤个十来分钟,唠几句家常便由姑父或表哥表弟领上,去给族亲拜年。我去的少,各家都不认识,就只记得大门大概的模样。原来还有老式弧形的门脸,雕刻着吉鸟祥兽牡丹仙鹤蝙蝠什么的,门口还有被岁月抹去眉眼的石狮子,后来再看不到了。都是瓷砖拼粘起来的大门,照碑墙巨幅瓷砖拼起的富贵牡丹或仙鹤贺寿,看起来富丽堂皇,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家里有狗的都早早栓在柴房。早些年还有养狐狸梅花鹿荷兰鼠的,也趁机看个新鲜。见面多介绍是谁来拜年来了,今天这一天来拜年的多半是“某某村的外甥”,然后磕头行礼,主家要上前做搀扶状说着“来了就有了”,掏了香烟说“换一支抽”之类的客套话。我不抽烟,大我一两岁的哥哥们就跟我说,要是好烟就接着,回头给我抽,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烟,他们会说什么中华啊三五红塔山什么的,最次也得是钻石,钻石又分金钻银钻红钻蓝钻,价格高低各不同,我听得一头雾水。回到姑姑家,姑父已经摆好宴席,过年天天设宴并不是多么丰盛,都是买现成的卤鸡酥鱼,再炒一个蒜薹炒肉或其他什么菜就算齐了,都不是外人,吃喝随意。酒是必须要喝的,三五盅浅饮低酌,一口辣酒下肚口腔里瞬间腾起一个火团,顺着食道钻进胃里,又迅速蔓延至全身。大姑或二姑做完饭也围坐在一起,说说一年的辛劳,在远方的儿女,不尽如意的收成,新年度的计划,火焰映照着喝过酒的脸庞更加红润,似乎这一切便是生活的一切得失。

初三回娘家,全家收拾利索,带上点心和要交换的花卷包子,一路打着招呼说着拜年话,多半公里就到姥姥家。一家给姥姥姥爷拜过年,我们兄妹给舅舅妗子拜过年,领过压岁钱,就跟着出去给姥爷的族亲拜年。小时拜年就是跟着淘气玩,另外看谁家有什么新奇的零食,不顾大人的呵斥往兜里塞。再有一条就是放鞭炮,把整挂的拆开了点,一颗一颗放,燃了长香,先是塞再墙缝儿里战战兢兢去点,年龄大些直接手拿着点,火捻一红就撒手扔天上,啪的一声,欢乐无限。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童年那么快乐,为一声脆响无比雀跃,不是因为破碎,而是基于一秒钟的存在感。啪!我点的。啪!它为我而响。啪!所有烟消云散。即是玩伴又是同学的死党表哥也是我在姥姥家欢乐的原因之一,只不过我回姥姥家的日子也是他回姥姥家的日子,总是碰不上。今年他说起一件趣事,那年初二他带我去他姥姥家,姥姥给了一块钱的压岁钱,硬是让他用五毛钱换走了,我还蒙在鼓里,我记忆里完全没有丝毫的影像,说明我要么太小了,要么太傻了。可我知道即使只有五毛钱也能买到现在五千块都买不到的美好。郑二孬,还我那五毛钱,犹大蒙蔽了上帝,你蒙蔽了我……

初四依旧是走亲戚拜年的日子,这次就换成了父亲的姑舅家,多半是我们这一代都不甚走动的亲戚,由大爷或父亲带领着我们去拜年喝酒。过年像是一张亲戚关系联络图,由亲至疏,荡漾着人际关系的美好涟漪。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兄妹会随着母亲去姥姥家。按照风俗正月初五为“破五”,不走亲戚,可初五是姥爷的生日,必须要给姥爷拜寿,所以初四就得去。所谓拜寿,无谓是全家聚到一起包顿饺子喝喝酒什么的,过年期间饺子都吃腻了,就换做长寿的手擀面,或熬一锅菜,蒙上早已熬好的海带猪肉。姥爷辛劳了一辈子,田间劳作之外,早年还是红白喜事做饭的一把好手。闲下来就戴上眼镜找一本书研究三皇五帝民国文革诸多黑白是非,在他心里自便明晰。也常常跟我讲些故事,如果有文学启蒙人一说,那姥爷当之无愧。时至今日,他年近八十,已沉重伛偻,吃完止痛药继续做着自行车轮胎代加工的手工。每次给老人买礼物都十足犯愁,给姥爷拿过两次五粮液黄金酒,希望他停下来小酌一二两,这岁月微醺才对得起自己的曾经风霜雨雪。姥爷啊,老骥莫伏枥,不如去看戏啊……老了,就该颐养天年,没病没灾就是对儿女最大的福祉了。姥姥眼睛有点玻璃体混浊,总是止不住的流眼泪,我在网上买了日本产的眼药水,希望她在不悲伤的时候不再流泪。听姥爷说,即便是吃了安定片俩人总是睡到三四点就睡不着了,漆黑的夜里听得见时光破碎的声响吗?

初六以后,年味稍淡了些,做些小买卖的都是今天或初八这种吉利日子开业开工,要去城市谋生的小弟弟妹妹们都打扮的光鲜亮丽准备拼车、转车回到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去继续做他们一时半会醒不了的梦。打工是我们这代农村孩子的主旋律,表姐在北京照相机厂当过流水线工人回来带过好吃的日本豆,武哥在北京当过保安回家三天还在说着令人仰望的普通话,大哥也去长春伐过树鄂尔多斯装过通风管道,妹妹还去保定包过水饺现在在北京当红牛饮料的业务员,我也在邻县自行车鞍座厂当过整整一年的挂簧工。我们是不再耕种的农民,一亩田除去种子、化肥、浇地、农药、收割、脱粒等成本,不算人工平均利润两三百元,十亩地不如打工一个月,这是年轻人不断离开故土的主要原因。城市的扩大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大量涌入,我们成为城市的外来物种,常年生活在城市,这里却没有立锥之地,故乡还给我们留了一间祖屋,我们却只想回到祖屋里怀旧,而不是生活。长得好看的或一身能耐的姑娘多半离开故乡就再不回去了,小伙子们却不得不因为各种硬件残缺最终回到故乡娶亲生子,可因适龄姑娘大量外流,剩下的本地姑娘人以稀为贵,逐渐水涨船高,彩礼从十年前的一万涨到了现在的十三万、十五万,还有置房买车,没有三四十万根本别想娶媳妇。据说谁家吵架闹离婚,第二天就有人上门说亲,彩礼照初婚给,大盘涨停,二手媳妇也奇货可居,到底是谁露出了马脚?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亿万个彩色泡沫包围我们的生活,在没有围墙的城市里,我们被困在薄薄的身份证里。

除了初十这天是老鼠娶亲晚上要关路灯之外,直到正月十五都没有什么新奇的与年相关的仪式或习俗,一切看起来涟漪散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就连门口的红对联都被淘气的孩子扯去了半拉,“春满庭院福满门”只剩下“福满门”,“春”被叠成纸飞机飞走了。
直到正月十五年的最后一次狂欢来临。春打六九头,到了十五,天气回暖,冰雪融化,桃树梨树的枝头都鼓着绿茸茸的芽苞,等待着绽放。早上吃花糕中午吃饺子放鞭炮后就要做一种传统的供品和小吃了。糜子面活好了上锅蒸熟,厚布包好了放在被子里火炉旁持续发酵。多半天后打开加糖再活,撒剂子做成各种形状,大多是圆柱体,上头凹下去,用纸包了火柴插在中间当火焾子,浇上棉籽油。也有其他形状的,比如两头花边跟公鸡头似的,还有蛇之类。天黑之后,一盏盏点燃,放在各个神位前供着。谓之“年灯”,一是过年的年,还是粘面做的“粘灯”。其中一盏要送到奶奶家祖宗神像前,我小心用手挡住风,别吹灭我的小火焰,万一吹灭了赶快回家重新点了,复往送之。晚上自是放烟火的季节,一条街不过四五百米,两岸挤满了人。早些年有专门组织放烟火的“灯笼会”,每年两家轮流值会,进腊月每天收一两块钱作为会费。小时的灯笼非常古典,是竹制纱围的,六格还是八格记不清楚了,上面是花草仕女,还有西游记人物什么的,里面点的是白蜡烛。当年还是坏小子的时候就曾偷过蜡烛,只为好玩。后来灯笼变成大红灯笼里面是一百度的灯泡,典雅尽失,倒是没人偷了,挂的奇高。收的会费大部分用在买烟花上,多是要买一车的。“火树银花”比较多,也有叫“孔雀开屏”的,由东至西,一字排开,璀璨的烟花冲上了夜空,带着轻快的爆炸声。孩子们手里拿着各种的看家烟花,小心翼翼地放着,“小蝴蝶”能从地上旋转着飞起来,“天女散花”飞到天上才轰然炸开,七色光焰宛如一朵大花。欢声笑语荡漾在好闻的硫磺味道中,孩子们去哄抢还在燃烧的烟火箱盒,淘气的大孩子就扔进去一挂鞭炮,孩子们四惊散去。意犹未尽时也要回到家中,把熄灭的年灯收集回来,案板上一压成饼,热了油锅放进去炸至金黄,外焦里糯,一口口都是年的味道。锅里水开了,煮半包黑芝麻馅儿的汤圆,连甜汤带汤圆吃个饱。爬到屋顶看远方还有烟花升腾,今晚月亮特别圆,圆得那么自然,圆得就像我刚刚吃的金黄的粘饼,我吃掉一个故乡的月亮吗?

十六一大早还有一个重要的风俗,称为“烤杂病”,很多地方都兴此风俗,只是叫法不同,据说源自女娲炼石。七八点钟起来,找巷口位置一把麦秸起火,再抱来棉花秸秆加火,把家里不用的旧扫帚之类的东西也扔进去。多是妇女老人,年轻人都赖床起不来。早些年每家都要把剩下的饺子、年灯拿几个过来,丢进火里烤。然后在火前拍拍胸、敲敲腿,念叨着吉祥话。接着从灰堆里扒拉出烤好的年灯、饺子互相给孩子们吃,说吃了饺子不冻耳朵之类的祝福。吃得老老小小嘴巴都是灰黑,用手背擦着,手背也灰黑,直到现在谁也擦不去这种记忆的斑点。火渐渐就灭了,人散去,剩下一堆黑灰,总有老人勤快,拿簸箕撮走,留下一块灰迹。至此年才算过完,最后一项如今也无人在遵循,就是等二月二回娘家那天早上,要把最后一个花糕吃掉,然后就开始摊煎饼,又薄又圆又香的煎饼。

快写完了,竟然有点失落,我在黑白文档里又过了一个年,或者把活着的所有年又过了一遍。我还尚未老去,为何总念着那些过往啊?我喜欢看国际频道播放的《记住乡愁》,其中那些村庄都重文宣武源远流长,往往青山绿水深宅大院,养育出众多英才大儒。而我的村庄名字很土,红砖灰瓦,别说省长院士将军明星了,连个乡长或者杀人犯都没诞生过。村前有条河还被填埋了,连同我摸鱼时的脚印和笑语都掩埋了。如今认识我的我认识的老人不断消失在熟悉的村庄里,如今那些年轻的孩子也不认识我,好像我从来不属于那个村庄。我是城市的外来物种,渐渐也沦为故乡的陌生人,所以每次回家我都赶到黄昏,才趁着朦胧的夜色去偷窃我丧失了时光。
五六岁光景时流行一种一米多细长的玩物,曰“手提花”,点燃一头就用力抡起,远看如同一个马戏团老虎钻的火圈,太小不懂玩法,点燃了就高高的举着,滚烫的烟花落在胸口,烫过棉衣,灼烧在胸口,离心脏只隔薄薄一层血肉。后借了邻家新鲜母乳几番涂抹方好,至今留在左胸口一块印记。所以,我是能记住这烟花烫的,一如不能忘怀看起来陈旧却美好的小小村庄。

此刻,北京的夜晚寂静无比,雾霾笼楼宇和星辰。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之中,物质欲望不断上升,内心的河流却往下游走,吃快餐的胃早已患上思乡的胃溃疡,不断分泌着叫做乡愁的病痛。我总是梦到亲人去世,然后从梦中哭醒,有一次我梦见自己死了,我挥舞着铁锹掘出一个方形的葬坑,亲手把自己埋进我家的麦地了。







李庆文:河北邯郸人,中国作协会员,空军退伍老兵,我来人间采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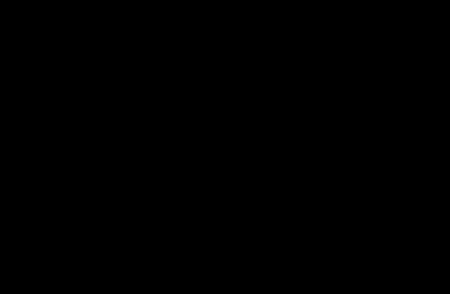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258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258号